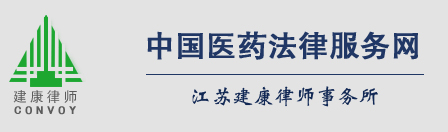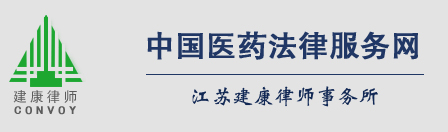对患者左足开放性骨折诊治不当致其截肢,
江苏两医院被判担同责
来源:中国医药法律服务网—江苏建康律师事务所
【简要案情】
2018年4月22日,原告王大有(化名)因在仪征工地上作业时坠落,一小时后至被告南京鼓楼医院集团仪征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仪征医院)就诊,当日予急诊行清创缝合+骨折内固定术,后收入院。入院时诊断:左跟骨骨折:左足第5趾近节趾骨骨折;左内踝皮肤撕裂伤。当日予急诊行清创缝合+骨折内固定术后。术后原告出现高热,创面流脓,周围红肿、压痛等症状,遂要求转院,2018年4月25日出院。
2018年4月26日,原告至被告南京同仁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同仁医院)就诊,拟“左跟骨开放性骨折-术后感染”收入院。原告入院后给予相关术前常规检查,治疗予以伤口切开换药,抗感染等保肢对症治疗,因考虑原告年纪较大保肢风险较高,被告建议截肢。2018年4月29日予以腰麻下行“左小腿截肢术”,2018年5月30日,原告出院。出院诊断:1、左跟骨骨折术后感染;2、左足第5趾骨骨折。
原告因对两医方医疗行为所导致的截肢后果持有异议,遂至本所咨询。本所主任、医学硕士王金宝律师在阅看有关记录后明确认为:两医方的医疗行为确实存在过错,与病情加重直至最后截肢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原告遂决定委托本所专业律师向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提起医疗赔偿诉讼。
【争议焦点】
患方认为(针对仪征医院):1、医方违反病历书写规范,无手术记录;2、抗生素使用严重违反规范;3、患者入院时无任何需要截肢的适应症;4、医方的过错导致患处肿胀明显及严重感染,是最后截肢的主要因素。
患方认为(针对同仁医院):1、抗生素使用存在不当,加重了感染的进展;2、未及时按照感染伤口进行处理,同样加重病情;3、患者入院时无明确截肢指征,医方的上述过错与最终的截肢存在因果关系,应是最后截肢的次要因素。
医方仪征医院认为:我院对患者处置及时,诊疗行为符合规范,与患者最后转归后果无因果关系,不应承担医疗损害责任。
医方同仁医院认为:我院诊断明确;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和义务;诊疗行为符合规范常规,患者左足感染坏死的损害后果与其严重外伤有关,与我院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
【鉴定意见】
受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的委托,2019年1月4日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认定:1、医方仪征医院对患者病情诊断欠准确;无清创手术记录,不能证明清创过程符合规范;对患处观察不仔细,检查不全面,未采取针对性治疗措施,存在医疗过错;2、医方同仁医院存在诊断欠准确、对患者入院病情未予重视、临床检查不全面、未采取针对性措施等过错;3、两医方上述过错和患者截止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过错的原因力为同等原因,其中仪征医院占90%,同仁医院占10%;4、患者损害经装配假肢后构成九级伤残;5、患者误工期限为180天,护理及营养期限各为90天。
本所主任、医学硕士王金宝律师作为患方代理人参加了本次鉴定听证会。
【一审判决】
2019年8月27日,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采信了上述医疗损害鉴定意见,判令两被告医院共同承担50%的赔偿责任,共计赔偿原告各项损失近18万元。
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生效。
【医事法律评析】
第一部分:南京鼓楼医院集团仪征医院存在严重过错,与患者左足感染的发生、进行性加重以及最终的截肢后果存在关系,且应为患者损害后果的主要因素。
一、医方违反病历书写规范,无手术记录,不能证明其实施的“清创缝合+骨折内固定术”符合技术操作规范,应推定其存在过错。
患者系在2018年4月22日下午伤后一小时余(18时许)先到医方急诊就诊。医方在行X线摄片后,即在腰麻下实施了“清创缝合+骨折内固定术”(麻醉记录等仅记载为“清创缝合术”),但无论是急诊病历还是住院病历中,均无本次手术的操作实施记录。虽然4月22日20:48病程记录有所记载,但仅为“术中见足底内侧动脉内侧支血管破裂,予结扎,左跟骨骨折,予两根2.0mm克氏针固定,余清创后逐层缝合,放置16mm引流管一根引流”,因此医方既不能证明其是先进行彻底清创后再行内固定,更不能证明其清创术操作过程符合规范。麻醉记录也不能显示其实际的手术实施步骤。
诊疗规范对于开放性伤口或开放性骨折的处理有明确的要求:常有污染,应行清创术,为组织愈合创造良好条件;彻底的清创是防止感染的关键;伤后6-8小时内清创一般都可达到一期愈合;规定了详尽的清创步骤,包括清洗、消毒、切除创缘、清除异物、切除坏死和失活组织等,使污染的伤口变成清洁伤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组织的修复。而且骨折的固定,也应当在彻底清创的基础上进行。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必须保护包括骨在内的活体组织的血液供应,以免导致......感染的发生(第8版《外科学》教材第136页;中华医学会编著的《临床诊疗指南•创伤学分册》第586、662页)。
二、医方抗生素使用严重违反规范。
创伤处理规范明确规定:对于开放性骨折,应防止厌氧菌感染;抗生素的使用应符合早期、足量、广谱的原则,在取得创口污染细菌培养结果后,立即改用敏感的抗生素(《临床诊疗指南•创伤学分册》第587页)。
依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制定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15年版)》,患者入院时的手术切口类别属于II类切口(清洁-污染手术),需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第4页)。给药方法:静脉输注应在皮肤、黏膜切开前0.5~1小时内或麻醉开始时给药,在输注完毕后开始手术,保证手术部位暴露时局部组织中抗菌药物已达到足以杀灭手术过程中沾染细菌的药物浓度。预防用药维持时间:抗菌药物的有效覆盖时间应包括整个手术过程。清洁-污染手术和污染手术的预防用药时间均为24小时,污染手术必要时延长至48小时。
对照上述规范,医方存在下列过错:
一是急诊手术前后均未使用抗生素。急诊病历以及术后的入院记录中没有记载抗生素的使用情况。
二是术后第二天上午才应用抗生素,存在明确延迟,不可能起到应有的预防感染的作用。根据医嘱单,医方首次抗生素使用为4月23日上午注射用头孢呋辛钠,4月24日上午感染加重后更换为哌拉西林舒巴坦钠+左氧氟沙星。
中华医学会编著的《临床技术操作规范•骨科学分册》明确规定如下:必须记住的是,抗生素决不能代替清创术或严格的无菌操作(第253页);不能因为有了抗生素预防而不认真准备皮肤、严格执行无菌技术和细致的手术操作(第251页)。医方不仅未能按照清创术的规范实施操作(详见前述),抗生素的使用又严重违反规范要求,因此患者发生严重感染显然是在所难免的。
三、其他过错。
一是从4月23日主任医师查房记录记载的“留置引流管在位通畅,引流出400ml暗红色血性液体”,可以确定医方术中对于足底内侧动脉内侧支血管破裂,虽予结扎,但未能充分结扎止血,或未能探查到其他可能的出血部位,导致患处肿胀明显及严重感染。
二是在进行抗菌治疗前,未依照规范先留取伤口部位的标本送检,直到4月24日上午才留取脓液送检,4月26日培养结果为“革兰氏阳性杆菌生长”。
四、患者入院时无任何需要截肢的适应症。
截肢的适应症为:1、肿瘤;2、创伤:急性创伤造成肢体严重缺血而无法修复者或严重创伤完全丧失功能者等;3、经治疗无效的急性或慢性感染有时需要截肢,如爆发性气性坏疽;4、血管疾病: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等;5、神经损伤后修复失败者;6、先天性畸形。根据《肢体损伤严重程度评分》表,假如肢体评分为7-12,则最终需要截肢;评分为3-6,可以保肢(《临床技术操作规范•骨科学分册》第208-210页)。
患者受伤1小时入院时,在骨和(或)软组织损伤、休克、缺血以及年龄等四个因素中,除了开放性骨折以及年龄大于50岁各评定2分,以及足背动脉搏动减弱评1分,共计5分外,并无其他加分因素,更无明确感染存在,因此完全适合于保肢治疗。
第二部分:南京同仁医院医疗行为同样存在明显过错,与患者截肢后果也存在关系,应是患者损害的次要因素。
一、抗生素使用存在不当,加重了感染的进展。
患者4月26日仪征医院细菌培养结果为“革兰氏阳性杆菌生长”,而医方在4月26日患者入院时所用的注射用头孢他啶,属于第三代头孢,适用于敏感肠杆菌科细菌等革兰氏阴性杆菌所致的严重感染,而奥硝唑仅用于厌氧菌感染。4月28日上午才加用了对革兰氏阳性菌有活性的替考拉宁,而此时医方已经决定行左小腿截肢治疗(见术前小结和术前讨论记录)。
二、未及时按照感染伤口进行处理,同样加重病情。
患者入院当日下午,医方请南京军区总医院专家会诊,建议“拆除VSD,伤口减压、引流,给予有效抗生素治疗,密切观察伤肢血运及全身情况,必要时急诊行截肢手术”。
除了上述抗生素使用不当之外,医方并未立即按照专家会诊建议处理,而是迟至4月27日上午才“拆除伤口敷料......予以床旁急诊行左足切开清创处理”,存在明显延迟,势必加重患者病情。而且由于清创处理无较为详尽的记录,只能从4月27日的医嘱知道是为患者实施了“特大换药”,因此医方不能证明其处理符合规范,应推定其存在过错。
三、患者入院时无明确截肢指征,医方的上述过错与最终的截肢存在因果关系。
患者4月26日入院时,伤口处虽有明显感染,但并不属于治疗无效,更不属于气性坏疽;而且肢体损伤程度评分最多为6分,仍有较大的保肢可能;医方的上述过错对于患者而言属于“雪上加霜”,与最后的截肢存在因果关系,应为患者损害的次要因素。